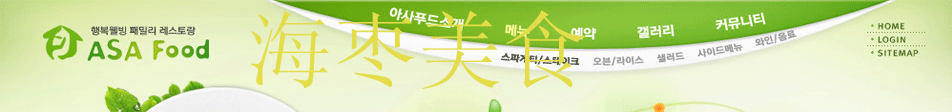|
彭洋医术怎么样 https://m.39.net/disease/a_9203314.html 再论“胜”及“胜形饰” 虎魄造办处 虎魄造办处——致力于学习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制品。 要研究“胜”及“胜形饰”,就脱离不了西王母。主观上都认为,“胜“即代表了西王母,其实不是。纵观西汉中期到南北朝,从西王母形象的转形、兴盛、衰落到最后与佛教融合。在这几百年时间里,西王母形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中,产生了无数的形象变化。可以说,西王母形象在这几百年里,没有统一标准化,其中亦包括“戴胜”形象和“胜”的造型。先由《山海经》记载中半人半兽的形象,向汉代贵族妇女形象转变。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逐渐添加一些当时的道教神仙思想元素。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还在演化过程中融入了很多外来元素。 最早成为西王母题材元素的应该是蟾蜍、玉兔、九尾狐、三足乌和“胜”,随后出现了胁侍、羽人、华盖、天柱台,再然后又添加了龙虎坐骑、伏羲女娲、肩部飘带(羽翼)。在四川地区,个别西王母形象还受佛教元素所影响。到南北朝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中,出现了佛道儒等多元一体的艺术。此时对西王母的崇拜已经衰落,西王母形象开始与其它的宗教艺术文化相融合。 到了唐以后,西王母定格为王母娘娘,仙界所有仙女之首,并掌管着吃一个便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蟠桃园。这个时候的王母娘娘似乎跟“胜”,和其它的各种形象元素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而与之相关的主要职能没变。 所以,纵观西王母形象的演化过程,那些附加在其身上的各种元素,跟当时当地(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信仰的需要而人为附加上去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西王母的神化地位而进行的人为“包装”。所以在这几百年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西王母形象。 成也大汉,败也大汉。西王母成为中国第一神,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兴盛于西汉晚期,又随着大汉帝国的灭亡而衰落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起,西王母这个曾经第一神亦被边缘化。 再回过头来看看西王母演化过程中附加的“胜”,虽然在西王母形象中出现的机率比较大,并被认为是西王母形象中最重要的元素。有意思的是,有很多西王母形象头上并非“戴胜”。更有意思的是,西王母头上所戴之“胜”并不是统一标准化的。因此,“戴胜”并不是西王母形象的绝对元素。西王母形象在转型到贵族妇女形象后,汉代人不断的进行艺术创作,“戴胜”即是创作过程中的元素之一。可能汉代时候的人们在为西王母转型的时候,也不知道“戴胜”具体是什么样的。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头上“戴胜”的形象。而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戴胜”造型应该起源于西汉晚期,西王母形象的发展在此时达到了顶峰。王莽为了篡夺西汉政权,对王政君和西王母进行了大量的“神化”和“包装”。个人认为“扁胜饰”与西王母的结合正是由此开始。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胜”亦与其它宗教元素相结合。所以,“戴胜”是西王母形象的元素之一,但并不是西王母形象的绝对元素。因此,“胜”也并非绝对的代表了西王母。 作为“胜形饰”,国内学者将其与西王母联系,主观上认为就是本土的产物。但是我认为其实是由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来的一种“护身符”性质的珠饰。在以合浦为主的两广地区,及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发现一种“扁胜饰”。而且主要由琥珀、绿柱石、多色水晶等异域材质制作而成。并且从加工制作工艺来看,与同时期贸易进入合浦地区的同类材质珠子一样都是外来的。 而且从目前考古出土文物来看,这种“扁胜饰”造型出现的时间最早,与后来两胜之间中间间距变大的其它“胜形饰”而言,明显有个演变过程。而反之东汉及魏晋时期出现各种千奇百怪的“胜形饰”却不见于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 在当时,汉帝国是丝绸之路上珠饰的输入国,而不是输出国。我相信在当时,没有理由会将绿柱石、多色水晶等此类域外材质贸易到合浦后,再加工成“扁胜饰”返销回东南亚。当时的合浦乃至整个大汉帝国,对玛瑙和绿柱石类的材质,在加工和制作上远没有域外先进和成熟。反之,如果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现玉质的“扁胜饰”。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由当时的汉帝国制作,并输出到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各国。 另外,从出土文物来看,在岭南以外的中国境内很少发现“扁胜饰”。而像绿柱石、石榴石、紫水晶等材质的珠饰,在除两广及湖南以外的中国境内也是十分罕见的。所以,毋庸置疑,最早出现的这种由绿柱石等材质加工制作的“扁胜饰”造型,就是由东南亚某地区加工制作后贸易进入当时以合浦为主的两广地区。 做为异域的“护身符”,输入汉帝国疆域后,与狮(虎)形等其它造型的“护身符”一样,被汉文化逐渐吸收并融入到汉文化中。另外,“胜形饰”与狮(虎)形等其它造型的“护身符”同时期出现在以合浦为主的两广地区,并同时期向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证据来看。很显然就是同时期由域外传入后,在原来域外的造型上进行了“汉化”仿制。所以,后来的“胜形饰”和狮“虎”形饰也亦逐渐的中原化,并进行了大量的演化。也正是此时,“胜形饰”的造型被西王母形象吸收并融入。同时期的狮(虎)形饰物也出现了天禄造型的演化。而这些演化后的“胜形饰”和带角带翅膀的兽形饰也仅出现于汉帝国的疆域内。 另外,有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微雕小动物的起源问题,基本上一致认为是受东南亚地区所影响后仿制的。那么,属于同一时期出现的“胜形饰”,亦也应该是受影响后仿制的。而这种造型的“胜形饰”在西汉中期以前是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它也不会是凭空出现的,亦不会是汉代时期的人凭自己的想像能力而创造出一个“胜”来。 有关“胜”与“勝”通假,并普遍存在“胜”由汉代织机上的构件“勝”演化而来的说法。我在全国各地的画像石上确实是收集到不少一些带有“勝”的东汉画像石,这些画像石中,有部分织机上的“卷经轴”的造型确实与“胜”一样。同时,全国各地的汉墓中同样也出土了汉代的织机。然后在这些出土的织机构件中,目前并没有发现与画像石上一样的“胜”形“卷经轴”。并且,这些画像石出现的年代比这些织机的年代要晚。又同样晚于西王母头上“戴胜”形象和“胜形饰”的出现。所以从现在的证据链来看,可能也是东汉时期,在织机上面“引用”了“胜形纹饰”。而其它的由“玉琮”、“西王母头上的三青鸟”演化过来的一些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从广西合浦县堂排M2号和母猪岭M4号西汉晚期墓所出土的这两条串饰来看,里面的各种造型珠饰在西汉中期以前的中原地区是找不到痕迹的。特别是一些动物造型的饰物,一眼看上去就不是典型的中原风格。而此类异域风格的动物形珠饰,从出土文物资料来看,在除岭南地区以外的中原地区非常罕见。而同样中原地区出现的那些演化后的“胜形饰”,和带角带翅膀的兽形饰在岭南地区亦非常罕见。与此同时,合浦地区与东南亚的贸易来往直到东晋时期一直没有断过。如果是贸易输出,这些在中原地区的饰物却没有或极少出现于岭南地区。更没有出现在越南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 如果说,之前提到的那些由绿柱石制作的“扁胜饰”是由当时汉帝国制作并贸易到东南亚地区的。那么,后来那些典型“汉化”后的各种造型“胜形饰”及“天禄”造型的各种兽形饰为什么不向东南亚地区输出?东南亚及印度等地区本来就是此类“护身符”的文化和加工制作源头,显然,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逆差。 所以,合浦即便有加工制作作坊,也是吸收异域珠饰文化与中原本土文化融合后,进行了“汉化”仿制,并有选择性的向中原地区输入。而“胜形饰”能在西汉晚期开始广泛传播也正是搭上了西王母这趟快车,并逐渐向全国发展并形成各种演化。 前面详细的解析了西王母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融入了国内外的各种文化元素。这其中就包括了将“扁胜饰”这种异域珠饰吸收演化后,形成“胜”并融入到西王母“戴胜”的形象中,同时并演化出各种各样的“胜形饰”和“胜形纹饰”。 又随着汉帝国的灭亡,佛教、祆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对西王母的崇拜开始衰落。“胜形饰”及“胜形纹饰”亦被其它文化所吸收和融入。比如十六国时期鲜卑族的马具和双马牌饰上;还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畏兽衔胜”、“双鱼衔胜”、“双凤衔胜”;最后还出现在青州地区北齐佛造像中。同时作为一种单独的纹饰普遍出现于东汉晚期到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的画像石(砖)上。所以,作为织机上的一个构件,并不足矣让这种纹饰如此普遍的传播和使用。 这种造型的“胜”和“胜形饰”与西王母的结合、演化与分离,都是历史发展下的产物。虽然它的诞生与西王母无关,但它的传播与兴盛却离不开西王母。哪怕西王母信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衰落,但“胜”、“胜形饰”及“胜形纹饰”却始终在各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文化中延续。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 特别鸣谢虎魄造办处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