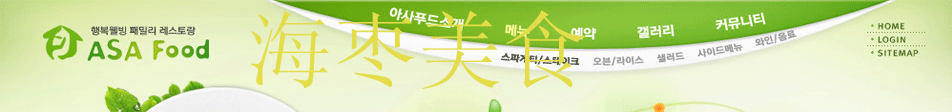|
青少年患白癫疯 http://pf.39.net/bdfyy/zqbdf/141112/4515785.html 「本文来源:南海网海南新闻」 班固像。 《汉书》。 《白虎通义》。 国画《班昭像》。 文\海南日报记者邵长春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作者是东汉的史学家班固,而鲜为人知的是,关于这部著作的编撰,远不止班固一人。 《汉书》与海南也颇有渊源,正史乃至古代典籍中大篇幅提及讨论海南相关议题,正是自《汉书》始。那么《汉书》又是如何谈及海南的呢? 本期《古籍新读》带您走近班固和他的《汉书》。 班固其人 班固,字孟起,出生于公元32年,东汉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祖先是楚人,秦末汉初,班家迁徙至北境边地,畜养牛马数千群,成为当地豪族。 汉成帝时,班固曾祖父班况的女儿被选入宫,封为婕妤,班家由此成为皇亲国戚,还被赐予皇宫图书副本,这是很大的荣誉,要知道当时连汉成帝的叔父——东平思王刘宇上书求取《史记》和诸子书籍都未获批准。 这批图书当时就吸引了大批学者登门造访,并为后来班彪、班固父子撰写《汉书》提供了重要基础。 班固的父亲班彪是两汉之际的儒学大师,个性恬淡,短暂出仕后即辞官归隐,专心著述,班彪认为《史记》只记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虽有后人补著,但言辞鄙俗,无法与《史记》媲美,于是班彪续采西汉遗事,傍贯异闻,作《史记后传》数十篇。 班固自小就在这样浓烈的学术氛围中长大,他聪慧过人,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名思想家王充年轻时曾拜访班家,见到13岁的班固,拍着他的后背对班彪说:“这孩子将来必定要书写汉朝的历史。” 班彪去世时,班固只有23岁,他离开太学回家守丧,由于认为父亲所续前史未详,班固开始潜心著述《汉书》,但不久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书稿也被没收。 班固的弟弟班超,也就是后来那个投笔从戎、立功西域、万里封侯的“猛人”,担心兄长在监狱里无法辨明冤屈,就飞奔到皇宫上书伸冤,得到汉明帝召见。 汉明帝听了班超的辩词,又看了《汉书》初稿,对班固才华很赏识,赦免了他,并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让其参与完成东汉本朝的《世祖本纪》、功臣传和两汉之际各种割据势力的载记,此书后经东汉历代不断补充,形成《东观汉记》,首开官修当代史先河,并成为后来范晔等人撰写《后汉书》的基础。 完成该项工作后,汉明帝命班固继续写作《汉书》。有了在宫内藏书处兰台工作的便利,班固得以大量阅读典籍,前后用了20多年时间,基本写就《汉书》。 班固的才华不仅限于史学,其创作的《两都赋》被《昭明文选》列为首篇;汉章帝曾召开白虎观会议,召集官员和儒生“讲议五经异同”,会议辩论的结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一书,对后世儒学有着重要影响。 班固收集了大量档案资料,用了毕生心血,终于完成《汉书》的纪传以及志的大部分,然而由于他平日疏于对家人的管教,其家奴在酒醉之后辱骂洛阳令种兢,种下祸根。公元92年,外戚权臣窦宪失势自杀,牵连众多,而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种兢借机报复,逮捕了班固,不久班固即死于狱中,年仅61岁,此时《汉书》表志部分还未最终完成。在《汉书》面临“烂尾”之际,班家兄妹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小妹班昭挺身而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父辈和兄长熏陶的班昭,对儒家经典和各种史籍耳熟能详,著名的《女诫》就是出自她之手。班固死后,汉和帝将《汉书》中《八表》的编撰交给了班昭,下诏安排她到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东观藏书阁抄录。除班昭外,在《汉书》的编撰收尾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马续。马续是伏波将军马援的侄孙,也是著名经学家马融之弟,马融就曾跟班昭学习。马续本人自幼聪明好学,七岁时能理解《论语》,十三岁懂得《尚书》,十六岁学习《诗经》。他博览群书,特别是精通《九章算术》,因此在班固死后承担了与数学密切相关的《汉书·天文志》续写工作。 《汉书》其书 《汉书》叙述了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近年的历史,共计篇,由十二纪、八表、十志和七十传四部分组成,体例上基本沿袭了《史记》纪传体的结构,但弃用了“世家”。 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目的有别,《汉书》断西汉一代为史,集中反映了西汉王朝的兴衰,开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此后历代正史基本上都遵循了《汉书》的体例。 《汉书》名列“前四史”,其叙事风格严谨,言语精炼,史料价值高,历来受到后人推崇,班固也和司马迁并称为“班马”。 《汉书》在叙事时间上有和《史记》重复的地方,对于西汉王朝前半期的史实,班固大多是直接照抄了司马迁的文字,但也有所创新,比如首创《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八表”中则增加了《百官公卿表》等,对于后世了解西汉典章制度都大有裨益。 而对于列传的编排顺序,《汉书》改变了司马迁的以排序明褒贬的方式,以时间为序,先专传,后类传,再边疆传,外戚传,最后以篡国的王莽和自序性的《叙传》收尾。 由于时代不同,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影响,他在评价司马迁时,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是部信史的同时,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即后世所谓的“史公三失”,引发了“班马之争”。 但在《后汉书》作者范晔看来,班固在陈述史实方面,不毁誉过当,不随波逐流,富而不杂,详细而有条理,人读而不厌;但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的是非观却显得有些轻视仁义了。 《汉书》多为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其中唐朝颜师古注《汉书》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汉书》与海南 值得一提的是,《汉书》与海南有着颇深的关系,正史乃至古代典籍中大篇幅提及讨论海南相关议题,正是自《汉书》始。 《史记》的《南越列传》虽然提及汉朝平定南越后,在南越故地设置九郡,但并没有一一列出九郡的名称;只是在《货殖列传》等个别篇中才出现了“儋耳”,也是一笔带过。 而在《汉书》的《武帝纪》《昭帝纪》《元帝纪》《地理志》《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多个篇章中均提到了海南。 《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海南的地理人文有着详细的记载: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 而《汉书》中篇幅最长、对海南的建置讨论最多,影响颇深的莫过于《贾捐之传》。 此后几百年里,海南岛上的建置多有反复,但因为再没有类似《汉书》这样的详细记载,很多事已然成谜,令人叹息。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